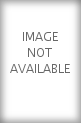
孔恩(Kuhn)在1962所出版的《科學革命的結構》在科學哲學與歷史(Philosophy and History of Science)領域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此書所得到的讚美和批評可以等量齊觀。《科學革命的結構》用寓建設於幻滅的循環來描述自然科學的演進。科學的演進可以分成三部曲。首先是「常態」科學(normal science):科學家們在共享同一個典範下的社群中分工解決典範所指引的謎題 – 在此時期科學的累積和進步最為明顯。但也就是這樣的常態科學會導引一個典範找出自己的不完美之處 – 科學家會在細緻化的研究中發現越來越多典範所無法解釋的異常現象(anomalies)。很多科學家會把異常現象歸因自己實驗的缺陷,或是把他視為典範所指引的另一個謎題(puzzle)。但是有部分的(尤其是年輕剛入行的)科學家開始質疑原有典範,並開始尋找新典範。當異常現象累積到一個程度,常態科學告一段落而科學革命時期開始:科學社群對典範的態度從少部分科學家的質疑變成百家爭鳴的辯論,直到新典範開始有能力「說服」大部分科學家改宗(conversion)為止。得到新一代科學家認可的新典範重新建立常態科學的各種規矩 – 謎題方向、答案格式以及社群規範,並重新開始另一個循環。孔恩利用了自然科學發展的例子,尤其是天文學(e.g. 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論至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論)與物理學(牛頓物理學至愛因斯坦物理學),來反駁過去對於科學發展乃是線性累積並不斷進步的看法。孔恩的研究一開始想要理解的是一個矛盾 – 為什麼亞里斯多德這位在眾多學科都留下深刻影響的智者,會在物理學說了這麼多荒謬的話呢?還有為什麼亞理斯多德的物理學可以支配人心兩千年直到牛頓力學的誕生?
孔恩利用典範(paradigm)這個概念來理解這個問題。關於典範一詞所遭受的批評可以說是最多的,而其他學者斷章取義或是另加詮釋也自不在話下。對孔恩來說,一個典範就是一個科學社群成員所共享的「東西」,反言之,一個科學社群即由一群共享一個典範的人所組成。這個「東西」可以被理解為這個科學社群所使用的特定共通語言、共享例證(exemplar)和共享世界觀。這個典範透過科學教育(如教科書)的方式讓學子們熟悉,並成為進入該科學社群的必要條件。另一方面,共享典範也決定了什麼樣的研究問題及成果能夠被該社群所接受。簡言之,典範定義了該社群所能看到的現象與所期待的答案。
瞭解一個科學社群所謂的重要研究問題以及他們所提出的答案的先決條件是瞭解他們的典範。換言之,要能理解該典範成員所使用的語言。孔恩回答亞里斯多德矛盾的線索在於他的偶然領悟 – 當他在1947年夏天反覆翻閱那本他認為全部是錯誤的亞里斯多德物理學時,突然發覺他能讀懂這本書了。他知道亞里斯多德為什麼問這樣的問題,也知道他的回答為什麼「合理」。換言之,孔恩戲劇性的學會從亞里斯多德的「典範」或「語言」來看亞里斯多德「所能看到」的物理現象,過去認為荒謬的語句立刻變成合理的了。
孔恩在科學史上的重要貢獻就在於利用典範這個概念來描繪自然科學演進的過程。共享一個典範的科學社群成員會不斷的遵循該典範來細緻化他們的研究,這也就是所謂的「正常科學」時期 – 科學在此時有明顯的累積性和進步證據。眾多科學家窮畢生心力去回答根據該典範所指引的謎題。但隨著研究問題的深化與細緻化,很多與典範相衝突的異常現象會出現 – 原有典範所期待的謎題答案沒有出現,甚至和原有典範產生矛盾。越來越多原本屬於該社群的科學家開始發覺他們共享的典範可能哪裡不對勁了。異常現象的累積將(雖不必然)促成科學革命的發生 – 部分科學家拋棄舊典範而開始尋找新典範。當一個新典範逐漸成形,它通常沒辦法說服老一代的科學家改宗 – 就和大多數人只能充分掌握一種母語一樣。但他可以透過科學教育的方式教育下一代科學家,並重新開始常態科學-異常現象累積-科學革命的循環。孔恩即用「典範轉移」來描述自然科學演進的過程。
孔恩還認為典範間具有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 – 科學革命前的典範和科學革命後的典範必定會有不可溝通的部分。不同典範對於該典範要解決的問題、可被接受答案的標準以及部分觀念的定義常有不同的意見。換言之,前後典範所屬的科學家所看到的是不一樣的世界,使用的也是不一樣的科學語言,想要回答的謎題和期待的答案也不一樣。這個不一樣可能是程度上的問題,但是孔恩強調這些不一致無法藉由一個前後典範都接受的說法來溝通 – 就像以中文為母語的人和與英語為母語的人並無法藉由另一種共通的(或中性的)語言來溝通。於是科學家只能選擇堅守原本的典範,或是選擇全面改宗投向新的典範 – 即使相當多的科學家都經常做不到改宗。達爾文在《物種原始》結尾的一段話可以做為如此態度的寫照:「雖然我完全相信這本書的真實性…,但是對於觀點與我完全相反的自然學者,我一點也不期望能使他們信服,他們心中以充滿他們的觀點引導他們去觀察的事物…但是我有信心面對未來,面對那些年輕、正在成長的自然學者,他們能夠公平的去看這個問題的兩面。」
孔恩將他所認為的自然科學演進過程描述的十分有說服力。批評者多半環繞在不可共量性與典範的精確定義,卻無法顛覆孔恩的核心思想。但是這套想法被運用在社會科學演進卻出現了很多爭論。有些學者引用孔恩的概念並認為社會科學一向處在前典範時期 – 學者們仍在百家爭鳴而沒有所謂共享的典範,當然也無所謂在常態科學下所累積的知識(參照(Feyerabend, 1975)對這群學者的批評);有些學者將典範觀念加以轉換,並用主觀/客觀的方式將社會科學中的研究分成了四種互斥不相容的典範 – 典範內學者各行其是卻不能彼此溝通(Burrell & Morgan, 1979);有些學者認為社會科學研究者應用多元主義(pluralism)突破不可共量性 – 用更包容的方式來讓社會中的各種價值能夠並存(Reed, 1985);當然也有學者反過來強調社會科學學派間的不可共量性(Jackson & Carter, 1991);或是如Willmott (1993)所倡導用辯證邏輯和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的方式來反思各個社會科學理論所遇見的異常現象與矛盾;更有甚者,如Dreyfus (1986) 所批評社會科學中根本沒有典範,只有一堆隨波逐流的理論風潮。這些對社會科學演進的探討,或許只說明了社會科學演進探討的迫切需要,而尚未出現一個能說服多數社會科學家的一家之言。當然,值得被探討不代表某種社會科學演進歷程必然存在或可以被描述 - 討論本身就是一個有趣的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