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意識地為自己活著,但卻同時是一個完成人類歷史普遍目的無意識的工具。
托爾斯泰
人類社會的紛擾從來沒有暫歇過,這些紛擾讓多少人投注畢生精力只為爭得一時的名利。但有沒有可能這些個體的爭名奪利到頭來只是為了完成一個更大的總體歷史目的?這其實不是一個新問題,時勢造英雄或是英雄造時勢本來就是一個難解甚至無解的謎。本書作者並沒有回答這個「歷史目的」可能為何,但他們為「何以中國從秦至清初的封建社會得以存在兩千年而幾乎一致?」的問題提供了一個相當科學的解答。用最淺顯的方式說,秦至清初的中國社會像一台可以設定自動重開機的電腦,當系統不穩定到一個程度,其會自動重新開機以回到初始設定的狀態。系統的支柱有三:大一統帝國官僚制度、地主經濟和儒家意識型態,重開機機制就是每兩至三百年的農民大起義。這樣的「超穩定系統」讓中國得以維持幾乎相同的體制達兩千年之久,直到西風東漸為止。
系統三個支柱的互相協調是系統得以保持運作的基本要求,其分別由政治結構(中央集權)、經濟結構(地主經濟)和意識型態結構(儒家文化)構成。每個結構都有相互牽連和影響的關係。中央政府賦予儒家思想正統的地位,而儒家進一步鞏固了中央集
宗族制也可以說明了地主經濟和儒家思想的關係。地主經濟相對於西方封建領主經濟最大的不同在於,在中國佃農和地主的關係是雇傭而非西方的奴俾,中國地主是不能隨意處置犯罪的佃農,必須要到官署控告,這也說明了中央集權的落實。而地主靠著族田和佃農上繳的租金維持整個宗族的經濟實力,但政治實力要靠著不斷培養年輕子弟上京應考,取得功名在朝當官,年老回到鄉里擔任仕紳,這些都是鞏固宗族繁盛的必要條件。管理中國一個最大的疑問就是中國這麼大,這麼有限的官僚數目怎麼可能管理呢?妙著就在於依靠儒家意識型態的操控,每個士人一輩子都心向朝廷,就算到了退休還是以鄉里仕紳的角色協助官府延續中央政府的管控,當然也繼續鼓勵宗族後進服從中央政府並考取功名。「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的確是這樣系統聯繫下最好的寫照。
但隨著朝代逐漸老化,系統間的聯繫會開始出現一些不穩定因素,作者稱之為「無組織力量」,最具代表性的無組織力量就是貪污和土地兼併。這可以以政治結構和經濟結構的互動來說明。朝代之初,前朝的地主都被殺光了,人口在動亂後也少了大半。倖存的人們可以各自劃地成為自耕農,或是集結四散的族人重新開始宗族的經營,這時大多數農民都屬於自耕農。隨著時間演進,以宗族為首的地主勢力大增,不論在經濟實力或是政治實力上,這些宗族於是開始兼併土地。中央政府在開國之初幾乎都不准土地的買賣,但是這些宗族隨著他們在中央政府掌控權力,這些開國宣示逐漸變成空話。隨著政府經營效率的下降和貪污的程度上升,一般沒有宗族支持的自耕農越來越難以自立更生,最能夠安家立命的方式就是將土地賣給宗族地主而區當佃農。所以佃農大量增加而自耕農大量減少多半是朝代邁入中期的證據。
很多朝代都有中興的紀錄,作者分析這是因為當時無組織力量尚在可以宣洩和補救的程度。中央政府尚未被宗族所代表的既得利益者完全掌控,佃農在地主手下又仍然能得到溫飽。但到了朝代晚期,無組織力量已經強大的任何改變都會是徒勞無功。在中央政府既得利益團體把持朝政,中央政令無法下達;地方也被宗族地主所操控,宗族地主稅收部分無法有效上繳的情況下,為了徵收因零星叛亂而增加的稅收,官府只能再進一步剝削剩下的自耕農。這一的結果就是官逼民反:剩下的自耕農算盤撥一撥,大不了橫豎一死,被你官府打死還不如我揭竿起義圖個痛快。於是,當無組織力量成長到一個程度,農民大起義於是反噬壓榨他們的宗族地主與地方政府。
農民起義對中央和皇帝通常還心存寄望,他們最直接的發洩對象都是地方官府、政府鷹爪和地方宗族。史冊上記載農民起義常伴隨著官府人員連夜逃跑,然後地方宗族整個被滅族。若只看到農民起義的慘忍,那可能就忽略了農民大多時候都是被壓榨的事實,還有農民大起義更重要的作用:去除無組織力量以恢復超穩定系統的初始狀態。無組織力量的兩個源頭在農民大起義幾乎都必然被消滅,貪污和土地兼併隨著宗族的破敗也回歸原點。起義結束的農民依然被儒家意識型態所掌控,他們是不得不起義,心中希望的還是有天子朝廷來領導,還有擁有自己土地的莊稼生活。多半農民起義完的朝代元老也的確能夠回應這樣的需求,於是乎開始了另一個超穩定系統的循環。
這樣的超穩定系統帶給了中國兩千年的相對西方穩定的璀璨文明,但缺點也是顯而易見的。誠如作者所言,這樣的系統讓中國封建社會沈浸在爛熟的文明中,失去了新生活方式的追求。中國文化是一個維護皇帝、聖人、老人、祖宗的絕對權威和古老傳統生活方式的社會,從這個角度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西方文明為什麼對中國的文明衝擊有這麼大,因為超穩定系統只能處理系統內生的問題,而處理不了外生的侵擾。作者的下一本書更有趣也更具爭議性:開放中的變遷。其試圖將清末至共黨專政的歷史一樣納入他們的大歷史觀中,不過那是另一篇的故事了。
用「超穩定系統」來瞭解中國古代社會的確很具說服力,每個歷史環節幾乎都被合理化了。但吸收了這樣的想法後不禁心裡揣揣,如果歷史的進程真如作者所言,那這樣的超穩定的系統一開始是如何被創造的呢?而中國兩千年歷史中的種種事件和人物,他們的作為和反應我們又該如何來解讀呢?弔詭之處在於,一個有說服力的歷史理論更讓人覺得人類的渺小與無知,更覺得眼下世界的紛擾是多麼的不值。如果說要給這本書一個我主觀的心得的話,就是我瞭解他們的解釋也願意接受中國歷史可以這樣被解釋。但我相信未來不會就此被決定的,過去能被解釋不代表未來就可以被預測。說到底,我仍是自由意識的服膺者和決定論的反對者。
對話錄 - 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
感謝Hello UK!版友提出不同看法。詳見http://www.hellouk.org/forum/index.php?showtopic=152593
Deer Paul:
使用某一種歸納法而得的理論 (如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又如文中所謂的 "超穩定系統", ~但其實這個字實在很有很有爭議性~) 能夠解釋歷史變化的真正原由嗎??? 把歷史變化解釋的合理是一回事, 但是歷史變化的真正因可能跟合理化的理論無關...每個歷史事件的發生似乎都有著其單獨的前因後果與獨特條件, 這些單獨的前因後果與獨特條件不一定可以依附在某一套有規律的理論來合理解釋, ... 這樣看來, 超穩定系統好像只是一套 "表面說辭", 而藏在"表面說辭"下的真正因可能會被這套 "表面說辭" 給模糊扭曲, 或是給過度粗糙或錯誤的解釋了。
Chengwei:
我非常能夠理解您的論點。這本書試圖提出一個系統化觀點來解釋這個大哉問:「為何秦至清初的中國封建系統得以維繫兩千年?」而三個結構耦合而行程的超穩定系統似乎的確可以回答這個問題。但也的確引起了更多疑問。若將您的回應換個方式表達,這本書其實在三個地方沒有表達清楚:理解 (understanding)、解釋(explanation)和預測(prediction)。
我在分享末正確的用語應該是我願意用他們的理論來「理解」中國古代歷史的進程,但這不代表他們的理論「解釋」了中國歷史,更不代表他們的理論可以「預測」任何未來事件的走向。理解是一種心理作用,我願意接受他們的理論來事後合理化所發生的事件;解釋的層次必須要提供事情發生的原因(cause)。而誠如您所說,我們或許永遠無法確定一個歷史事件發生的原因為何。更嚴重的是,一個可以事後合理化所發生事件的理論,絕對不代表未來可以根據該理論被預測!
他們的理論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屬於「決定論」的,也就是說,當ABC因素都出現,結果也必將是XYZ。但我不認為未來也會重複這樣的模式。這個議題又牽扯到了哲學上的另外一個根本議題:自由意志vs.決定論。若他們的理論完全正確,那在這個決定論的世界裡,人們將不再歌頌英雄,不再需要承擔道德責任,也不需要對未來做出更多思考和努力,因為一切已經是註定的。這樣的論點不是錯誤,而是不符合人類社會運作的基本假設和法則:我們通常都打從心裡感覺我們是自由的在做決定,也在很大程度上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所以我認為他們的理論雖然幫助我們「理解」中國歷史,但不應該被放大到一個決定論的層次:也就是該理論不能真正「解釋」,更遑論「預測」歷史的走向。
Skysayhigh:
如果照作者說,中國的封建社會是從秦到清初維持了兩千年,那是誰改變了這個系統?這絕對不是「西風東漸」四個字就能解釋的了的…那是當年的孫中山嗎?是的話,那想必孫中山必定摧毀瓦解了系統三大支柱中的其中之一或更多?地主經濟?官僚政治?還是儒家思想?孫中山靠的似乎也不完全是系統中重開機的農民起義…
一個存在並演化了兩千多年,同時經得起無數次重開機的系統(超穩定系統),必有其成熟性、穩定性和不可動搖性,然而這樣的「系統」卻在從清朝跨到民國,只在兩個「朝代」間就改變,而非經過更多時間(例如百年以上或是多個改朝換代)做系統轉換,我一直試著從決定論來試著解釋…
Chengwei:
我能理解您所說西風東漸不足以改變中國古代社會超穩定系統的問題。但作者的論點其實不是西方勢力改變了這個系統,而應該說是西方勢力就像是一種外來病毒破壞了整個中國社會原來可以自我修復的超穩定系統。超穩定系統的自我修復機制建立在系統的亂源來自於內生,比如說是中國社會自身的土地兼併及貪污腐敗。若擾亂系統的因素來自於外界,那系統自我修復機制將無法使逐漸破敗的系統恢復到初始狀態。
作者提供的論證和例子是魏晉南北朝。一個從最初研究問題延伸的子問題就是:為何魏晉南北朝中國分裂達三百年之久而無法恢復大一統王朝?這是超穩定系統假說的謬誤嗎?作者指出三點來說明魏晉南北朝乃是超穩定系統更新自我修復機制的過渡時期。第一,東漢末年雖有農民起義和暴亂,但並沒有完全將地主勢利和貪污腐化的根源掃清,取而代之的是軍閥割據,這樣的情況有將中國當時社會轉向西方封建領主制度的可能。第二,儒學在魏晉南北朝之時開始受到佛學的影響,而不像過去居於絕對主流的地位。第三,外族進入中原,也將其文化帶入中國古代社會。
作者的重點其實是後兩點,因為佛學和外族文化不是中國古代社會所既有,作者將這樣的外界力量視為對超穩定系統的挑戰。中國社會的特殊之處,就是在經過三百年的融合之後,儒學竟然可以再度中興並整合了外來的佛學,而也讓加入外族的中國古代社會重新接受了三個結構的耦合系統。最主要的更新出現於意識型態上,儒學在隋唐一代和漢代的儒學已有相當程度差異。總之,魏晉南北朝可以視為中國古代社會接受系統外來力量的挑戰,並以三百年的時間調控自身修補機制,並重新開啟一個新的超穩定系統循環。
若以這樣的角度來理解我們所身處的世界,或許共產專政意識型態和台灣及香港的亞民主意識型態*又只是中國社會面臨外界挑戰所產生的修補機制一環。我再次強調這只是理解過去發生事件的一種角度,它不必然解釋了真正的歷史,也不能預測(或決定)任何未來所會發生的事情,比如說大一統的中國。我們處於局中,就算是最出類拔萃的人,也只可以比擬曹操或諸葛亮之流之於魏晉時期,我們盡我們的知能去理解歷史,但卻對未來一無所知。然而這不代表我們不能創造歷史,我們只是不能準確預測而已。
但是,托爾斯泰有關歷史目的的箴言,仍會不停的縈繞每個試圖理解歷史的人心頭。
*我不確定台灣和香港的意識型態該用什麼方式來稱呼,姑且稱之為亞民主。
Justinchiu:
如果從合理性的角度來理解這一個所謂的超穩定結構,是否會有新的角度呢?例如怎樣才被認可為合理?所謂傳統中國的合理性為何?(但是這絕不代表所謂套用 Weber 而產生出所謂的儒家與東亞資本主義這種簡化與抄襲的詮釋,去看待合理性的建構,或許才是更重要的)或是從Foucault的啟發來看看,統治與知識、與對社會真實的建構之關係,所謂will to truth or will to knowledge是否在傳統中國也出現?治理很多和對於合理性、知識、真實與道德的建構有密且關係,在傳統中國這個部分的影響應該絕不輸於 Foucault 所講的。或是大陸近年在講的潛規則,是不是可以和Bourdieu 的habitus 或是political field 等觀念有一些可能的交織呢?
傳統中國的governmentality和知識與對於國家、社會與人認識論應該有很大的關係,重新從 governmentality的角度來檢討與思考,或許可以稍微減輕這個超穩定結構詮釋的些許武斷、類結構主義式的問題。想想這個好像可以成為一個很好的研究題目, Foucault的兩篇演講中,一個從前基督時代講起,另一個從現在國家的出現講起,那是不是也可以所謂的Chinese governmentality呢?
Chengwei:
一個說明或是解釋合不合理和具說服力,必須要考慮到幾個因素:第一,所引用的原因究竟存不存在所解釋的現象中;第二,所引用的原因是否是對所解釋的現象直接關連?(Big Bang可以視為所有現象的根因,但通常不會出現在一個你為什麼遲到的解釋中。)第三,根據聽眾的知識和動機,這樣的解釋是否足以滿足聽眾對所發生現象的疑問。以我閱讀這本書的想法,作者對中國歷史的說明確滿足了這三點。但我強調這是我的理解,而理解和我自身的動機、知識和需求相關,所以我不能期待別人對這本書也認為一樣的合理。
傅科的作品我只讀過皮毛,所以無法對您的見解做出回應。但我認為Anthony Giddens的Structuration理論有可能可以對超穩定系統一些沒講清楚的地方加以補足。尤其是結構是如何被人們建立,而已存的結構又如何回饋人們而進一步的影響人們的行動。至於潛規則,作者吳思先生的著作的確很引人入勝。我認為該論點很能說明中國社會個體間互動的規則,我所有興趣的是這樣的 規則能不能被超穩定系統這樣的總體理論所涵蓋,如此將可以加強超穩定系統假說對我而言的合理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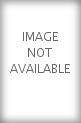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