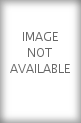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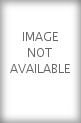
這是一本關於人們該如何解讀歷史的書。
托爾斯泰具有敏銳的觀察力,他能洞察人類社會錯綜複雜的因果關係網,卻仍希望能夠在這些紛亂中找到頭緒:一個不變的真理。對托爾斯泰而言,人類社會的運作遠比歷史學家的描述複雜。他那個時代的歷史學家說,拿破崙侵俄是由於他的野心,是由于俄皇的不妥協,是由於外交斡旋的失敗,是由於雙方將士想打仗升官。從每個不同人物的角度,上述的說法可能都在歷史進程中佔了部分的原因。但是如果我們從更高的角度來看,數百萬人從西方前進到東方燒殺擄掠,犯下了任何國家法律都會髮指的罪刑;然後數百萬人再從東方殺回西方,不到兩年間數百萬人喪失性命。歷史學家所提出的原因在這樣的歷史現象前未免顯的渺小與偏狹。托爾斯泰認為要理解歷史,要先接受每個歷史參與者都會對整個歷史進程有影響,就像物理學的合力是由每個個體的分力所構成一樣:每個個體都往其想要去的方向前進,而整體歷史走向卻不會是個體所能控制或掌握。拿破崙的個人意志並不比一個哥薩克騎兵的個人意志來的重要。為什麼?托爾斯泰用了整本書來說明這個道理。
故事的主軸發生在三個俄國家族。安德烈公爵出生於一個俄國望族,他的父親在他那一輩出類拔萃。而安德烈公爵也繼承了父親很多特點,希望能夠在作戰中建立軍功並飛黃騰達,為此他甚至可以犧牲家庭和視妻子為累贅。當然,之後無情的戰爭折磨並徹底改變了安德烈。第二個主角尼古拉伯爵生於一個輝煌一時卻逐漸沒落的俄國貴族家庭中。相對於安德烈的雄心壯志,尼古拉像個紈袴子弟。雖然也想要在驃騎兵中取得功名,但更多時候他對風花雪月更有興趣,並不顧家族正在衰落的事實我行我素。同樣,戰爭也沒有對尼古拉特別友善,他的家族不只走向破敗,他的愛情也不被祝福。在整本書裡面唯一可以說是始終如一的人物就是皮耶爾伯爵,他是俄國最有錢貴族的私生子。他父親在過世前,出乎眾人意料的將全部遺產留給了皮耶爾。他對錢和管理家業並沒有特別興趣,遂被彼得堡貪婪的貴族們予取予求。其後又被心懷鬼胎的公爵半強迫的娶了他漂亮的女兒,但不久就因妻子紅杏出牆而更對人生心灰意冷。他的長處是在於獨立思考,可以說是托爾斯泰的分身和表達托爾斯泰對時局看法的代言人。
除了藉由三個家族的興衰和經歷來描寫俄國當時的社會情況,托爾斯泰花了更多篇幅來描述戰爭。重點擺在兩場戰爭上,第一場是俄國聯合奧國及眾日耳曼盟邦和拿破崙的一戰,結局以拿破崙大獲全勝取得歐洲霸主作收。第二場是幾年後的拿破崙侵俄戰爭,從俄軍一路退守到反攻,換句話說,從法國聯軍光榮佔領莫斯科到一路退卻的戰事。根據托爾斯泰的描述,兩場戰爭的結果都不因任何個體的意志而有所直接影響,不論是三個主角、拿破崙、俄皇亞歷山大、雙方元帥們、或是士兵們。更嚴格來說,每個個體的行為都對結果有影響,但這些行為部分是個體有意識運作的結果,但更多的是個人無意識的本能。
拿破崙被稱為一代軍事天才,他的個人魅力及領導似乎獨領歐洲十年風騷。照法國歷史學家的描述,拿破崙在每場戰爭都洞燭機先,在第一線發號司令打擊敵人。但托爾斯泰根據史料重現了部分現場:戰場的混亂是戰爭最大的相似之處。以一場決定性會戰為例,拿破崙所發的所有命令到了前線都無法被執行,因為拿破崙根據前一刻所得到的戰情做出決策,當這個決策再傳達至前線時,前線情況已經完全不同。前線指揮官和將士只能根據本能,攻擊和逃跑都以能夠存活最主要目標,不難想像執行的結果常常和拿破崙的命令根本相反。簡言之,戰爭的過程和結果都和拿破崙個人的意志關連不大。我們若只從拿破崙的意志、軍情命令和戰史來解讀該段歷史事件,不免覺得一切都是這些偉人獨領風騷。托爾斯泰花費五年時光撰寫這本小說,就是要用各種史料證明一件事:要理解歷史,不能只研究偉人、英雄、皇帝,而要從市井小民、士兵和一般人開始,這樣才有可能瞭解所謂的歷史的規律。他所鄙棄的所謂歷史學家,是那些試圖事後合理化並用已經修飾後的史料作研究的那些學者。那樣的歷史,是屬於君王和作家們的歷史,而不是社會的歷史。
當一個歷史事件發生,我們多半只看到直接促成該歷史事件發生的意志,而忽略了更多未被執行的意志。比如說拿破崙最主要的敵人一直都是英國,為什麼最後拿破崙反而去攻打長期的盟邦俄國呢?托爾斯泰認為,一個意志或決策能不能被執行和它能不能符合眾多配合的因素有關。拿破崙攻擊英國的意志不能被執行,和成千上萬個個人意志的累積合力有關。拿破崙攻擊俄國成真,也和成千上萬的個人意志的合力有關。這樣就出現了一個矛盾,成千上萬個意志的合力和歷史目的的關係。意志的總和在當下往往是不可知的,每個人覺得自己根據自我意識自由在行動,但全部個體總匯集而成的意志流卻可能只是幫助完成某個目的的工具。如果是這樣,那個人的自我意志也不能說是完全自由的,個體的自由只是假象,歷史以某種灰暗不明的方式操縱了個人。
托爾斯泰認為,這個矛盾在我們對歷史因果關係的認識論。個人的意志究竟是自由的?還是遵循著某些不可知的歷史目的?他提出三點說明人們因為人類的某些心裡特性而會如是解讀歷史。第一,完成行為的人與外界的關係。關係越多,該人越不自由,其行為的必然性也就越強。比如說一個離群索居的人會被認為是最自由的,而如果我們在描述一個人的行為時將其周圍的各種條件都將以描述出來,像是他所讀的書、所認識的朋友、職務的背景等,我們所感知到的他的行為必然性就越強。第二,人們解讀一個人的行為是否自由和時間的因素有關。一個行為在發生的當下,往往會被認為是最自由的;若一個人回顧一年甚至十年前的行為,那該行為的必然性就變的很強了。因為個人得承認,若沒有遙遠過去的那個行為,就無法解釋現下的快樂、悲傷或是必要的結果。就總體論也一樣,我們很難想像沒有十字軍東征歐洲會怎麼發展,沒有秦始皇統一天下中國歷史會怎麼發展。最後,解讀人們行為的自由還與我們對人們該行為的的瞭解程度有關。越瞭解一個行為的原因,我們就會認為該行為越不自由。比如說若酗酒的行為均來自於基因的影響,則我們就不會毫無保留的指責酗酒行為,因為他有一定的必然性,酗酒的人並沒有不飲酒的自由,也因此不被認為要承擔所有的責任。
但不論如何,人的行為是不可能完全自由或是完全服從某種必然性的。完全自由相當於我們處在一個完全隨機的世界裡;而完全必然我們就不成為人。我的們意識希望自由,但理智又希望探索必然,人生的一切於是就處於這兩者的矛盾下。要理解歷史和人生的意義,於是要從承認這樣的矛盾開始。我們每個人都有影響歷史走向的自由和能力,但使整個歷史走向又不會是你、我或是任何人所能主導。歷史走向不是完全的必然,但眾人意志的合力多半是無法輕易瞭解的,在發生當下尤然。於是我們錯覺以為歷史有一定的目的導引人類,其實都源自人類理解歷史事件的認識論的盲點。
來自Hello UK的回應,請見
http://www.hellouk.org/forum/index.php?showtopic=154173
from Excalibur
幾年前我進入這個領域時, 我也是個外行人, 所以我的老師們一直嘟嚷著要我去修史方和史論.
很幸運地, 我沒修. 我沒有這個才華學習做一桌臭掉的菜, 還能讓一群人吃的津津有味.
我 思考了很久, 到底要不要回這系列的文章. Chengweiliu的文章很"專業", 許多國內歷史系所的老師和學生們都寫這種文章. 我讀了其他幾篇Paul的評論, 我心裡一直反覆地想著, 我是如何以一個外行人的身份自持, 而至於自傲. 我是否要以這種自傲的態度, 一腳踢翻這種文章?
"用火", 是個很平實很易懂的觀念. 自然界與人類之間存在許多"必然"的關係. 好比飲食, 不吃就得餓死. 有收穫就有分配, 也就有權力. 有災殃就有救濟和防衛, 也就有組織. 這些關係要如何透過文本來解讀和還原? 切記切記, 文本雖是傳統史學的基礎, 但文本陳述一個社會, 一個行為, 一個事件, 和一個組織的潛力極其有限. Chengweiliu以戰爭與和平為文本寫作托爾斯泰的歷史觀, 是建議將該文本以角色為基礎解構, 而後重組. 這犯下了兩個無法由文本看出的根本的錯誤. 第一, 這個文本的代表性為何? 第二, 歷史學家是否可能以每個參與歷史的角色的觀點陳述史事?
第 一, 代表性. 托爾斯泰是誰? 為什麼他的"小說"能陳述史實? 當然他沒有打過拿破崙戰爭, 他或許是以重現拿破崙戰爭實期的貴族間的利益及情愛糾葛寫出這本小說. 如果, 沒有其他的替代文本能更忠實地描述拿破崙戰爭, 托爾斯泰的小說就成了極其珍貴的史料, 如同荷馬的史詩, 如同聖經中的舊約. 但真的沒有替代的史料存在嗎? 在這種以文本為根據的研究法中, 存在一個極大的問題, 代表性? 這是文本研究法的死穴, 也是小生不屑以為本為根據的文化研究的主因. 研究者如何能確立幾個文本就代表一個時代, 一個階級, 或一種風潮? 以小生自己的研究為例, 英國中世紀著名的年鑑家Henry Knight寫到在黑死病後, 工資漲到兩三倍之高. 而Langland在The vision of Piers the Plowman中寫到Piers抱怨工人如何懶散和貪財. 二十世紀的史學家D. L. Farmer自140餘份莊園帳本中整理出的數據卻不作如是說法. 工資漲個兩倍就不得了了, 但大致仍符合中世紀文本的描述. 以此, 史學家多半抱持黑死病後的勞工法規在限制工資水準上的效果有限之論. 小生自己從Pittington和Elvethall帳本中摘下的資料則說明, 在某些地方就不是這麼回事. 這兩地的工資水準就一直沒超出法律規定的上限. 那麼, 中世紀的文本, 到此不是跌了一大跤? 而以文本為根據的解釋, 不是犯了錯誤了嗎? 事情可能沒那麼嚴重? 重點在於如何定義與限定文本的適用性, 以及, 這個定義要如何達成? 一本書就代表一個人所看到的世界, 他的世界就那麼大, 一個外人要如何替寫書的人定義他的世界? 不可能. 所以文本研究, 無用.
第二個問題來自"沒有實作經驗"這個國內西洋史研究的陳窠. 是的, 不要以為某國立大學教授頂著牛劍之名, 就一定有實作經驗. 傳統史學, 僅管在牛劍, 教的還是文本和解讀. 假設, 托爾斯泰所言均有所本, 換個題材, 他未必能使用原來的法方再做一遍, 因為他不見得找得到史料. 國內的歷史系的史方史論課程, 一直在教學生如何分析某某人的方法, 但從不講某某人如何"幸運地"得到可用的史料. 運氣, 在實作(experimentalist)史學中, 是主要的變因之一. 沒有資料支持某種方法, 某種方法在這個題材就無用. 分析別人的方法毫無意義, 除非研究者能取得與"別人"所使用的史料一樣品質的史料. 所以Chengweiliu這篇文章的目的為何? 托爾斯泰的方法有用? 還是托爾斯泰的資料有用? 又或者托爾斯泰的結論有用? 如果答案是任何一個, Chengweiliu都該重打三十大板. 如果他的老師給了他高分, 這個老師該被吊銷教師證, 然後抓去浸豬籠.
歷史不是文字遊戲, 但整個史學的大趨勢卻是倒向文字遊戲. 我分析原因, 發現主因是"技術能力欠佳". 一, 語言能力: 台灣不是沒有提供學者或學生出國蒐集資料的財源, 但學者或學生出國能蒐集什麼資料? 做近現代史的人幸運, 因為他們不用讀古文, 做古代史的人卻要鬧笑話, 因為他們讀不懂古文. 二, 分析能力: 歷史學的分析方法多半是借用其他領域的理論和方法. 受限於史料, 經濟理論成為最重要的依據, 但各位學經濟的知道, 經濟史學家的方法多半很"可笑". 這項technical barrier遠比語言的問題更重大, 因為史料的組織以及理論/結論的題出取決於論者對理論的掌握程度, 不懂理論卻精通古文的人, 與懂理論卻只能查字典的人的見的比起來, 就是外行, 就是會鬧笑話. 牛大的梅修教授在他早年的一篇有關MV=PT的文章中, 連方程式的定義都弄不清. 因為這層技術障礙太難突破, 辯證法或唯物辯證這種相對簡單的方法就成了史學家的最愛. 在英國, MA的學生第一個要學的就是辯論. 但小生不玩這種把戲, 因為我用我的右手和左手互打, 永遠也打不出"對"的那一支手. 想當然爾, 小生的偏激立場不太受學院派的欣賞, 但小生仍以不玩文字遊戲為傲.
這裡講太遠了, 回到原來的文章, 作者寫的很用心, 很專業. 但是, 任何一個受過嚴格的邏輯和科學教育的人都看的出來那種分析, 沒有半點真實的成份在. 而在另一個層次的歷史專業中, 我只能說, 那是為什麼"台灣沒有西洋史研究"的原因.
My reply:
我想您們的珍貴評論就是我當初發表的初衷。寫作是為了讓想法更多人接觸,而想法的交流是磨練思考的最佳途徑。不過在感謝Paul與Excalibur對我文章用心的評語之餘,我想要澄清兩件事情。第一,我完全是史學研究的外行人,我的專業是商業策略,我的系所是商學院,這篇文章完全沒有任何專業史學的成分在其中。第二,這篇文章不是作業也不會有人批改。其完全來自我讀完戰爭與和平後的心得,您們就是我唯一的評審。所以我的指導教授並不會有被浸豬籠之虞。以下我先針對Excalibur您的評語做出幾點回應。
1. 文本及文本的代表性
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中想要表達的其實和Excalibur您所提及您自己的研究有異曲同工之妙。托爾斯泰自己有經歷過克里米亞戰爭,他在自序中提及戰爭發生中的一切是多麼的混亂與無序-命令無法下達、戰情無法上傳、友軍砲火傷及我軍較敵火更嚴重等…而所有參與其事的人在發生當下都能體會這種混亂。但他的親身經驗告訴他,在戰事告一段落後,每個參謀都能寫出一份「合情合理」的報告,而這個報告層層上傳到司令部後就變成了官方說法。當官方說法成立之後,托爾斯泰再回頭問那些親身參與戰事混亂的士兵,他們反倒開始忘記了當初所經歷的混亂,而開始用「官方說法」來理解之前所發生的戰事-比如說因為某某將官的英明領導而讓俄軍重創英法聯軍,或是因為某元帥的蒞臨而穩住士氣使俄軍挺住陣線。
托爾斯泰寫這本著作的動機可以說來自於上述的親身經歷。回答Paul的問題,托爾斯泰的獨特貢獻在於指出理解歷史不能光用歷史學家所提供的「答案」-這些「答案」充滿了英雄、偉人、帝王、貴族和事後合理化的解釋。事後看來這些解釋或許「合情合理」,但就像克里米亞戰爭中參謀的報告一樣,那些答案根本沒有解釋任何事情,因為他們可能根本沒有發生過。探討戰爭與和平此書最好的評論家可能是牛津的俄裔哲學家以薩柏林。他說明托爾斯泰的真正主旨在於:(柏林慣用長句,直譯中文多半失去其鏗鏘有力的原文風格,所以我引用原文。)
“Tolstoy’s interest in history has arisen not from interest in the past as such, but from the desire to understand how and why things happen as they do and not otherwise, from discontent with those current explanations which do not explain, and leave the mind dissatisfied, from a tendency to doubt and place under suspicion and, if need be, reject whatever does not fully answer the question, to go to the root of every matter, at whatever cost." (1953: 10, emphases added)
托爾斯泰用戰爭與和平說明他的一個觀念-在他那個年代的歷史學家對拿破崙戰爭所提出的理論與解釋並不是「真的歷史」。人們要瞭解歷史真實的面目與走向不能只看那些「偉人」,而要從市井小民與販夫走卒下手。每個人的意志都對歷史的走向有影響,那些偉人們或許佔據了歷史舞台最醒目的位置,但他們的作為或許完全受制於眾人意志的合力-以此觀之,偉人們才是最不自由的一群。就像是一群野牛在奔跑,每隻牛都可以對群牛行進的方向做出部分即使微小的影響。但在群牛中的第一隻牛往往誤以為整群牛的方向是跟著牠的意志來行進的。托爾斯泰視拿破崙為十八世紀初歐洲領頭的呆頭牛,而視試圖用這頭呆頭牛來解釋十八世紀初歐洲史的歷史學家為他的主要思想敵人。
善用文本或許讓Excalibur所謂的文本研究有不一樣的貢獻。托爾斯泰利用他所能取得的文本-那些有關「一般人」的文本,來推翻那些歷史學家根據偉人作為的文本所得出的「歷史」。托爾斯泰在全書中沒有斷言他所描繪的是「真實的歷史」,但他所撰寫的小說足以讓他那個時代的歷史學家所撰寫的歷史變成偏頗的「偉人史」而非「真實歷史」。這就是為何我說托爾斯泰的論點和Excalibur所提出的黑死病後工資變化的例子有異曲同工之妙的原因-再詳實的文本研究代表性都不足以建構真實歷史,但善用文本足以推翻錯誤的歷史解讀。
2. 史學方法論與文字遊戲
我想我的文章並沒有提到史學方法論,文章的目的單純的只是介紹托爾斯泰解讀歷史的角度。戰爭與和平是本厚重巨作,有興趣把她看完的是少數;而整部小說我認為的精華在於小說的尾聲,也就是托爾斯泰將其寫作動機娓娓道來的部分。很遺憾的,很大一部份坊間戰爭與和平的版本都把這部分刪除了。原因很簡單,托爾斯泰在尾聲與歷史因果論相關的論述牽涉哲學、心理學與歷史學,而和小說本身格格不入。所以本篇文章的目的僅在此-介紹托爾斯泰這部分的想法分享給更多人,而並沒有深入史學方法論的問題。但以外行人的角度來評論,托爾斯泰的方法還有資料還是有他的價值。誠如上段所言,適宜的文本研究足以推翻錯誤的歷史解讀。而他的結論更是我們在思考現下局勢的一個好觀點-眾人的合力究竟要把我們帶往哪裡?而檯面上的人物究竟和托爾斯泰筆下的呆頭牛們有何差異?我私以為真實歷史是無法窮盡的,再好的研究方法都只能讓我們得到一個較好的「歷史詮釋」。這不只是史學,在商業研究以至於大部分的社會科學恐怕都有一樣的問題。在我們否定任何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可以導引我們至「真實歷史」的同時,我們應該要開放心胸允許任何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都有帶領我們至一個較好的「歷史詮釋」的可能。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